
2014年5月19日,为庆祝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九十周岁生日,罗斯柴尔德基金会(Rothschild Foundation)主席雅各布·罗斯柴尔德(Jacob Rothschild)邀请杜维明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进了一场有关文明对话与多元文明的演讲。在演讲中,杜维明正式提出“精神人文主义(spiritual humanism)”的理念。精神人文主义,是杜维明六十余年来致力于儒家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思想结晶,是儒学第三期取得的开创性进展,也是“建构具有全球性普世意义的当代儒学”的重要基石(foundation)。

作为全球最具前瞻性和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杜维明先生著述颇丰,或由其原创、或经其开显而广为人知的众多论域,大都超出学术领域,走向大众成为了“公共话语(public discourse)”。为更好地理解精神人文主义,或许我们可以从杜先生的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两个方面谈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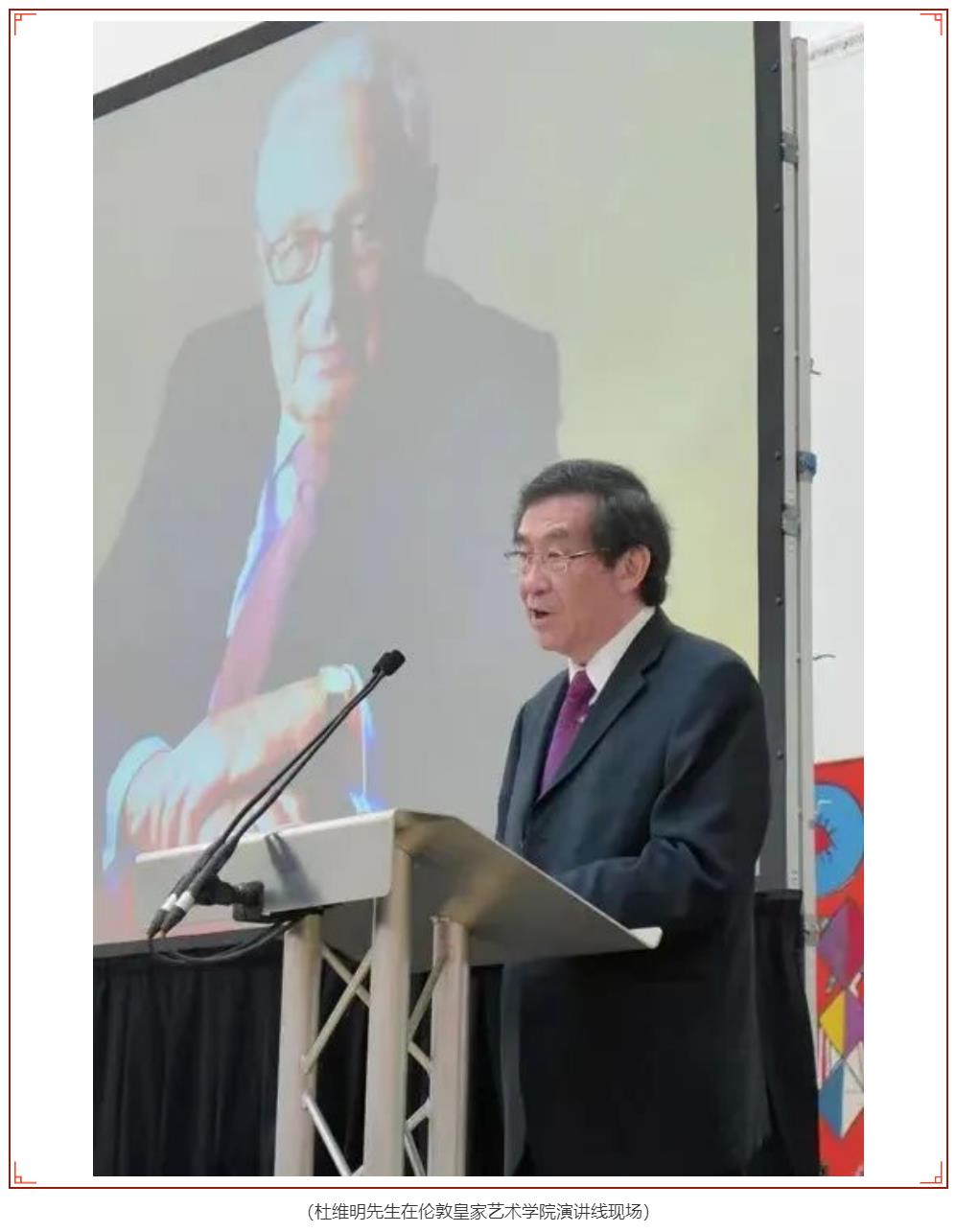
首先是文化自觉,杜维明视1981年移教哈佛为人生转折点。先前,他通过在中国台湾东海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的学习,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学与研究,对儒家核心价值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他“近三十年悉心耕耘的论域”提供了厚实的精神资源。移教哈佛以后,他又“主动自觉”踏上“根植儒家传统,在现代西化的大潮中,关注‘文化中国’,面对人类的困境,通过文明对话,为儒学第三期发展,走出一条较为宽阔的道路” 的新征程。自1986年重提“儒学第三期以来”,杜维明先生就将“能否对整个西方文明、尤其是启蒙以来的‘启蒙心态’做出回应,能否给人类社会提出有价值的思想资源”视作21世纪儒学发展的关键。杜维明注意到凡俗人文主义大行其道产生了诸多弊端,他自陈“我提出了宏大叙事,是源于我的忧患意识,自觉地和越分越细、越走越专业的学风背道而驰”。他相继开显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启蒙反思、工业东亚、全球伦理等“觉他”性的论域,“在这几个论域所形成的‘启发性对话’(edifying conversation)的氛围中,儒家哲学所体现的‘精神性人文主义’获得了发展空间”。
其次,是方法的自觉。对杜维明而言,方法自觉大致可以分两个层次,一是学术研究的方法论的自觉,二是学术生涯“做哲学” 的自觉。杜维明认为,“与外在世界毫不发生关涉的专家学者,不是我最向往的‘人格形态’”,“如果学术界不能拥有影响大众、教育大众和导引大众的消息力量,研究的动源接着就枯竭了。而动源一枯竭,学术研究就变成了考据游戏,没有宗教的关切,也没有哲学的智慧,只剩下一些只宜束之于高阁的档案”。杜维明将会议、演讲、面谈和访问视为精神磨练的不可或缺的功课,他“主动选择了一条自以为符合儒家身心性命之学的‘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道路”,成为一名行动的儒家(Confucian in action) 。
杜维明认为,“做哲学(do philosophy)”和“研究哲学(study philosophy)”是两条不同的道路,重要的哲学家,都是在做哲学。在他看来,“认为自己只是追求纯粹的客观,而把事实与价值(fact and value)完全分开的人,常常是偏见特别深而懵然不知的人”。杜维明自觉继承其业师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所开展的根植于儒家心性之学的道路,以文明对话之姿、思启蒙心态之失、纠主客二元之偏,转凡俗人文主义之弊,基于儒家这一“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知识”,建构了精神人文主义理论:“精神人文主义是对人性的信仰(faith),学以成人是为达致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因为超越与内在本是不二的”。

(书法家金鸣先生书)
杜维明说,“作为精神人文主义的儒家,提出了每一个有良知理性的知识人都必须关注的四大议题”:
(一)个人的身体、心知、灵觉与神明如何融会贯通;
(二)人与人之间如何通过家庭、社会、国家和世界形成健康的互动;
(三)人类和自然如何取得持久的和谐;
(四)人心与天道如何相辅相成。
精神人文主义所体现出的,是对一种非此即彼的“排斥性的二分法”的超越。根据我的理解,我们可以从以下五个维度对其进行解读:
继承性与超越性的统一
精神人文主义,继承启蒙精神,但是超越启蒙心态,体现出继承性与超越性的统一。杜维明认为,启蒙精神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具活力和转化能力的思想意识,其本身蕴含着现代社会之所以成立的重要价值基础,是人类觉性的一大标志,诸如自由、平等、人权、个人尊严、尊重隐私等价值;科学技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领域,都与启蒙精神密不可分,进一步深入扩展启蒙的积极价值必不可少。但是,启蒙心态所导向的人类中心主义也是人类现今根本困境的源头——理性人、经济人概念将人化约成抽象的个体,忽 略了对人具体性和复杂性的全面了解;宗族主义、民族主义、宗教派别主义将人类撕扯成不断分裂的群体,失去了国家、民族、宗教间的共识;人不再满足于做大自然的一分子,而成为自然的征服者并最终被反噬;人对自我力量的无限期待,消解了任何具有神圣和精神性的存在,因而,也必须对其进行深刻反思。
根源性与开放性的统一
精神人文主义根植于儒家传统,也向全球所有的精神文明开放,体现出根源性与开放性的统一。这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文化中国传统内部,杜维明反复强调,儒家不应也从来没有一枝独秀,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是丰富充实的,佛教、道教、民间信仰等精神传统,都是我们思考现代问题的起点。另一方面,对于世界其他精神文明,诸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耆那教,还有全球各种诸如印第安人、夏威夷人、毛利人、非洲人所信仰的本土宗教,都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资源。精神人文主义涵摄了上述方面,是一种整全的思维模式和理论架构。
在地性与普世性的统一
精神人文主义,虽然源于儒家传统这一文化中国的地方价值,但同时也具有普世意义,体现出在地性与普世性的统一。杜维明视儒家传统为“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价值(local value with global significance)”,儒家虽然有其特有的表达语句、存有形态,但儒家所蕴含的学做人的道理,根植于普遍的、具体的人性,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资源。未来文明的发展,必然是多元多样的,但又不能是特殊分裂的,而应建基于对话之上,相互理解和尊重。儒家没有两种语言, 即一种宗教的语言,一种世俗的语言,儒家从来只有根植于生活世界学做人的语言。一个人可以是美国人、伊朗人,可以是基督徒、伊斯兰教徒,但不可以选择不做人。学做人,是儒家的核心关切,也是其普世性的源泉。
精神性与凡俗性的统一
精神人文主义,关注精神的面向,强调“天人合一”,但儒家并没有一个彼岸的世界,是“以凡俗为神圣”的精神传统。儒家认为,当下的凡俗世界,是我们修身和转化的起点,同时也是终点。儒家认为,“没有一个独立于自己修身养性之外独立存在的罪恶”,在儒家之外的精神文明中,神圣与世俗是截然分开的,佛教的红尘与净土、基督教的天国与俗世,儒家不存在截然区别的两个世界。因而,精神人文主义的儒家,既关注精神性与自然、对宗教有体认有敬畏,也认为当下是唯一的存在与真实。儒家认为,只有通过修身的行为实践,才能体现最高的价值,也就是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精神人文主义并非一套理论的施设,而是实实在在的“知行合一”之说。精神人文主义是儒家主动自觉面对启蒙心态下现代西方凡俗化的人文主义,从心性儒学入手,以文明对话的开放心态,反思儒家及其现实意义的思想,也是涵摄性的开放体系,能为人的全面发展、人类的持久存续和共同繁荣提供参照。精神人文主义不仅是一个思想体系,“更是一条生命哲学的实践道路(杜维明语)”。
本文作者 | 陈茂泽
北京大学哲学博士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Copyright@2014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京ICP备案1253235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五号北京大学李兆基人文学苑4号楼 技术支持:iWing